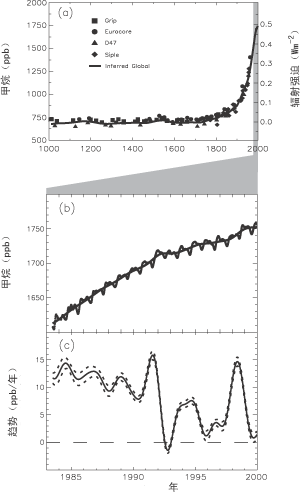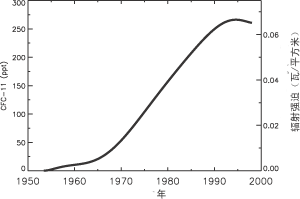甲烷(CH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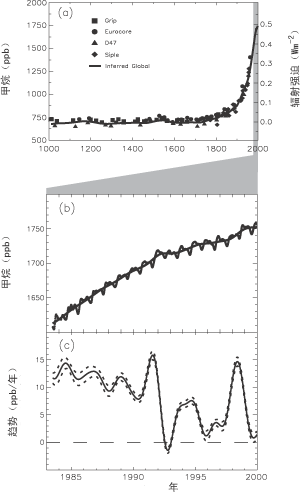
图11: (a) 由冰芯、积雪和整体空气样品画出过去1000年CH4浓度变化(摩尔比,按ppb = 10-9)。在右坐标轴上显示出自工业革命以来辐射强迫几乎是线性增加。(b)1983-1999年全球平均CH4浓度的月平均(逐月变化)和季节平均(光滑线)。(c)从1983年至1999年全球大气甲烷浓度年增长速率。其计算是根据上述季节变化趋势曲线推导而得。不确定性为±1个标准偏差。[根据图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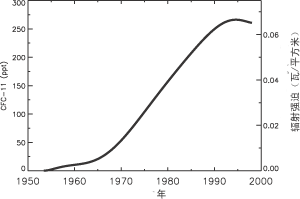
图12: 根据平滑后的观测值和排放模式得出的1950-1998年的全球平均CFC-11(CFCl3)的对流层浓度(ppt)。右侧坐标轴表示CFC-11的辐射强迫。[根据图4.6] |
甲烷(CH4)浓度自1750年以来增加了150%(1060ppb),但过去42万年里目前的甲烷浓度没有被超过。甲烷(CH4)是一种温室气体,它既有自然源(如湿地),也有人为源(如农业,天然气开发,废弃物等)。大气中目前大约一半稍多的甲烷排放来自人为源。它们通过化学反应从大气中清除。如图11所示,自1983年以来大气甲烷浓度全球有代表性的系统观测业已开展。人们还从冰芯和岩石层中获得样品,从而推算出很久以前的大气中甲烷的浓度。目前甲烷的直接辐射强迫是0.48Wm-2,大约是全球长寿命且均匀混合气体贡献总量的20%(参见图9)。
大气甲烷含量持续增加,从1983年的1610ppb到1998年的1745ppb,但观测到的年增加率在这期间却在减少。年增加率在20世纪90年代变化很大,其中,1992年几乎为零,1998年为13ppb。目前对这种变化没有明确的定量解释。自从SAR以来,人们对某些甲烷的人为源,例如水稻田,有了更精确的研究。
大气甲烷浓度增加速率是根据没有完全了解清楚的源和汇之间的很小偏差计算得到的,这使得人们对未来大气甲烷浓度的预测变得困难。虽然影响全球甲烷收支的主要因素已经被识别,但从定量的角度看它们大部分还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估计多变的生物源排放率十分困难。对甲烷的源强的定量和定性的了解的有限限制了人们根据任何给定的人为排放情景对未来大气甲烷浓度的预测(也相应地限制了辐射强迫贡献的预测),特别是因为甲烷的自然排放和清除相当大地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氧化亚氮 (N2O)
氧化亚氮(N2O)的大气浓度自工业革命以来稳步增长,目前比1750年增加16%(46ppb)。但目前其浓度在至少过去一千年里是最大的。氧化亚氮是一种既有自然源又有人为源的另一种温室气体。它在大气中主要通过化学反应清除。大气中氧化亚氮的增加速率持续在0.25%/年(1980至1998年)。业已观测到氧化亚氮浓度增加有明显的年际变化,例如从1991到1993年间年增长率减少50%。可能的原因有:与氮有关的肥料使用的减少;生物源排放的减小:由于火山爆发引起大气环流的变化所带来的大范围平流层的消失等等。自1993年以来,氧化亚氮浓度的增加速率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观测值。这种观测到的多年变化周期对我们了解控制大气氧化亚氮的过程有所帮助。至今,我们仍不能解释这种温室气体多年变化趋势。
与SAR相比,氧化亚氮的全球收支处于较好的平衡状态,但单个源排放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氧化亚氮自然源的排放估计大约是10TgN/年(1990年),其中土壤贡献大约65%,海洋贡献大约30%。现在,新的、估计更高的人为源(如农业,生物质燃烧,工业活动以及牲畜管理)排放大约为7TgN/年,与SAR相比,这使源与汇估计趋于平衡。然而,自SAR以来,对这种长寿命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可预测性认识并没有明显的改进。它对辐射强迫的贡献大约是0.15Wm-2,是长寿命且全球均匀分布温室气体总量的6%(参见图9)。
卤化碳及其有关化合物
这些气体既能使得臭氧消失又对温室效应有贡献,自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限制它们的排放以来,它们在大气在的浓度有的在减少(如CFC-11,CFC-113,CH3CCl3和CCl4),有的缓慢增加(如CFC-12)。许多卤化碳还是有辐射活性而且长寿命的温室气体。卤化碳是由碳和氟、氯、溴、碘等合成的化合物。人类活动是这些化合物大部分唯一的源。含有氯的卤化碳(如氟里昂-CFC)和含有溴的卤化碳(如哈龙)对平流层臭氧有耗损破坏作用,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受到控制。在1994年对流层中臭氧消耗气体总量达到极大值,随后逐渐减小。一些重要的卤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已经达到峰值,参见有关CFC-11的图12。对流层中CFC和卤化碳的浓度与报告的排放相一致。卤化碳对辐射强迫的贡献是0.34Wm-2,这是全球均匀混合温室气体贡献的14%。(图9)
观测表明,CFC替代品的大气浓度正在增加,许多这些替代品都是温室气体。HCFC和HFC含量的增加来源于它们早期的持续使用以及作为CFC替代品的使用。例如,HFC-23的浓度在1978至1995年期间增加了2倍。因为目前的浓度相对较低,HFC对辐射强迫的贡献还相对较小。HCFC对辐射强迫的贡献也很小。所有这些气体未来的排放都受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限制。
PFC(如CF4和C2F6)和SF6也是人为产生,它们大气寿命非常长,对红外辐射有强吸收。所以这些化合物虽然它们的排放量较小,但对未来气候的影响很大。CF4在大气中可以至少存留50000年。它有自然源,但目前的人为排放是自然源的1000倍多,并是观测到的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每千克单位基础上,一个SF6分子的温室效应是CO2分子的22200倍。虽然它目前的大气浓度较低(4.2ppt),但它的增长速率明显(0.24ppt/年)。观测到的SF6增长率与根据销售和储存数据而计算所得的排放十分一致。